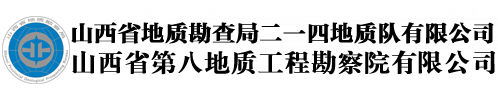

扫一扫,更快捷、更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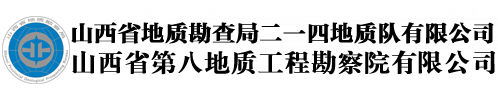

——读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有感
这段时间一直沉浸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这本书所表达的情感及其语言魅力深深吸引了我。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无病呻吟,他的每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在调侃中述说,每一篇文章总有那么一点自嘲和嘲他。他用那些隐藏于角落不被人留意的琐碎事物衍生出生命的真谛,悟透人生的悲凉。
当读到《寒风吹彻》这篇文章时,我的内心仿佛比这个阴郁寒冷的冬天还要冷,尤其是这段时间,空气中每天弥漫着雾霾,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让人难受之极。
立冬刚过,白雪就忍不住的想要人们看到他美妙的身姿。那天早晨,我和作者一样“我把怕冷的东西都一一搬进屋子,糊好窗户,挂上去年冬天的棉门帘,寒风还是进来了,他比我更熟悉墙上的每一道裂缝”,我所在野外项目部的同事都不约而同地换上了过冬的衣服。这股寒流来的太着急了,以至于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准备“炉火”。这对我们这群从小没吃过苦的90后孩子来说,这样的环境实在太艰苦。一位老师傅给我们讲了他们以前野外工作的场景,零下几十度的天气,帐篷只能挡风,不能保暖,躺在被窝里都瑟瑟发抖,户外作业更是辛苦,寒风吹到脸上跟刀割一样生疼,尽管如此艰苦,但是依然没有人请假或者退出,他们只担心怕天气再冷下去会影响正常的钻探工作。有时为了取暖,他们会架起一堆火。“柴火在火中啪啪燃烧着,炉火通红,我的手和脸都发烫了,但是火只是把身体正面烤热了,脊背依旧凉飕飕的”刘亮程的描述和师傅的讲述经如何贴近,我被他的文字感染,也被地质工作者的精神打动。
作者用四十万字去描述他的精神寄托——黄沙梁,看似刘亮程在书中描述的是黄沙梁的鸡鸭猫狗、驴马牛羊、草木鱼虫、风土山水,但是作者说到“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认为弄懂了他们,其实我懂了我自己”。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过冬”,人的悲剧似乎在于,想远离孤独,很多时候却跳不出孤独。作者在《孤独的声音》中这样写道“离开野地后,我再没见过和那只灰鸟一样的鸟,这种鸟可能就剩下那一只了,他没有了同类,希望找一个能听懂他话语的生命。他曾经找到了我,在我耳边说了那么多动听的鸟语,可我,只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没在天上飞过,没在高高的枝头上站过,我怎会听懂鸟说的事情呢?”这里所隐喻的或许是他内心孤独的感受吧,在那样贫瘠、闭塞的地方,人们只知道春种秋收,只知道一日三餐,只知道“牲畜、草木、天气、一小片阳光、吃、劳动、睡觉,除了这些再没啥想头”,这平实的日子,大概没人关心什么散文啊,文学的。那种找不到“同类”的内心的荒芜感,何止“孤独”二字。
在《狗这一辈子》中,他写道“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太厉害不行,太懦弱不行,不解人意,善解人意均不行。总之,稍一马虎便会被人剥了皮炖了肉,狗本是看家护院的,更多时候却连自己都看不住。”看似在感叹狗的一生,其实笔笔道出的,不也是人间的沧桑吗?做人艰辛做人难!
刘亮程笔下的卑微生命,往往隐含着对人生意义的反思。《与虫共眠》中 “有些虫朝生暮死,有些仅有几天或几个月的短暂生命,几乎来不及干什么便匆匆离去,没时间盖房子,创造文化和艺术,没时间为自己和别人去着想,生命简洁到只剩下快乐,我们这些大生命却在漫长岁月中寻找痛苦和烦恼”。这段话无疑是对人类的极大讽刺,看似繁华的都市,喧闹的社会早已与最初的梦想背道而驰,渐行渐远,最终沦为“痛苦和烦恼”的代名词。
但刘亮程的黄沙梁分明美好,竟勾起了我对故乡的怀念。那是名叫子谏的贫穷又平实的村庄,丘陵错落,沟壑遍及,可挖窑而居,气候土壤适宜,适合梨树生长,号称天下酥梨第一村。每年的三、四月份,梨花就陆续开放,放眼望去,密匝层叠,如白云轻飘、雪花漫洒,空气中氤氲着淡淡的芬芳,沁人心肺,让人似喝醉醇酒,飘飘然了。到了七、八月份,黄澄澄的梨挂满枝头,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纷纷忙碌起来,年龄小的爬树摘梨,年龄大小心翼翼地把梨放到箱子里,生怕磕着一个。家乡的梨晶莹剔透,仔细端详可以透过薄薄的皮清楚地看到里面洁白的肉,便会忍不住想咬上一口,待牙齿碰到梨的瞬间,甘甜梨汁会迸发而出,清爽怡人。吃完梨必须立刻洗手,要是等梨汁干了,手指就跟抹了胶水一样,随你怎么样也挣脱不开。
我的父老乡亲,如同刘亮程所描写的那样,在看不到头的土岭和沟壑间一年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凭着辛劳,凭着智慧,依势凿穴、栽梨致富、生儿育女、生生不息。刘亮程这本散文集充满了乡土气息,又道尽人生哲理,让那个生养我的村庄在记忆中升腾起来,再回望时便发现许多新的景致、新的活力。《一个人的村庄》已然不再是一个人了。 (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