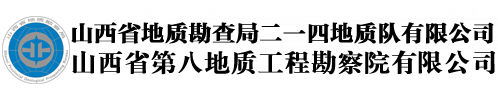

扫一扫,更快捷、更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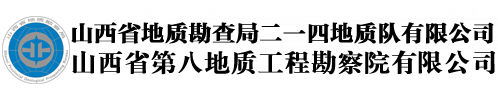

上山的路蜿蜒曲折,仿佛一条在绿海中舞动的黄丝带,望着峰回路转的山路若隐若现,秦胜利突然萌生了一种户外探险的欣喜。他甩开膀子,加快步伐,还时不时地查看手机信号。他出生在平原上的村落,这是平生第一次独自走进大山深处。“大山我来了,我要站到你的头顶上。”秦胜利向着大山深处呐喊。
正值正午,焦阳烈日,秦胜利眯着眼睛仰望天空,一朵棉花糖状的云朵像是在故意 “整蛊”他,上山前还在东边,没多大功夫,就闪到了西面。看来,他没有“享受”的命,只能忍受烈日煎熬了。
沿着山上高低不平的车辙印,老秦乞盼的目光向远方延伸,儿子说要来看他的时候,他竟高兴地忘了问几点钟到。没法子,老秦只能一有空闲就到站到山梁上张望。
秦胜利是老秦的儿子,85后,大学本科生,学得是土木工程。记得是在儿子出生后的第五天,老秦才匆匆赶回家,“我叫秦利,咱儿子天平饱满、地阁方圆,将来肯定比我强百倍,就叫秦胜利吧。超过他爹。”孩子他妈连忙“呸呸”两声,“啥名字呀。一点文化都没有。别人还以为是兄弟呢。”原本还一脸怒气的老婆,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老秦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钻工,二十多年前打井,现在依然如此,连他自己都认为自己除了打井啥也干不利索。老秦是工友们的“开心果”,他肚子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讲到动情时,他竟然能声情并貌,潸然泪下。老秦故事汇里最精彩的故事当属《出殡》了。当年,老秦刚到野外项目部时,正好赶上老李头退休。一顿饭,一场酒,老李头就兴高采烈地直奔山下。半个月后,他竟然神情沮丧地回来了。大家围着老李,好奇地问,“这好不容易熬到头了,要过儿孙满堂的好日子呀。你怎么又上山“落草”呀。”老李头哇地一声就哭了,眼泪比黄豆还大,那真是老泪纵横,“一家大小都对我爱搭不理。儿子不叫爸,孙子也不叫爷。这二三十年的罪白受了,今后的日子这可咋过呀。”钻机机长给老李出了个邪招,“直接叫你爸,孩子们别扭。孩子们与你的生疏其实就是层窗户纸。你回去后,按我说的来,肯定立马见效。血浓于水。孩子们见你那一招准蒙。”半个月后,老李头又回来了,追着机长骂道,“你个憨娃,让我给媳妇跪也就算了。还让我装哭,假装给孩子们认错。说什么这叫先入为主,釜底抽薪。搞得我们一家子哭了大半夜,让左右邻里以为我妈过去了。”
看着眼前的车辙印,老秦想到了自己,他的人生就如同这车辙般,总与最亲近的人处于平行状态,像是隔了一条跨不过去的天河。母亲去世时,他在工地,等回到家已经是五天以后了;妻子做手术时,他在路上,小舅子一脚就把他踢出了病房;儿子高考时,他又工伤住了院……。儿子胜利对老秦有种天然的排斥感,小的时候,胜利都不允许老秦进家门,更别说是睡一张床了。上初中的时候,胜利对老秦说,“我恨你,你连最起码的安全感都给不了我们。”面对儿子如此扎心的质问,老秦一句话也说不出口。至于以后,老秦连想都不敢想。因为他知道,有个老钻工到65岁,才等来孩子们的一声“爸爸”。
山路十八弯。秦胜利步行了近三个小时,才看见远处山坳里一块平地上停放着大大小小数十辆轿车,四周是迎风招展的彩旗。哎!终于到了。他一溜烟便冲下了山坡。
秦胜利现在已经上大四了,前些日子接到老秦打来的电话,说是在一个偏僻山村里打井,等完工了就去学校看他。老秦还高兴地告诉胜利,他们原本计划打水井,没想到竟然打出了地热,现在水样已经化验出来了,完全达标。电话那头传来老秦爽朗的笑声,秦胜利还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倾听父亲的笑声。他随即做出一个决定:“老秦,你们不是要搞典礼么,我想见识一下你们的地热井。”老秦正要说,山路难走时,那头已经挂了电话。按老秦说的地名,秦胜利在百度地图上找到那个叫“板峪”的山村。有个网友留言说,从公交终点站离板峪村有近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最好是乘摩的去。
对秦胜利来说,老秦更像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一个一年到头都见不了几回的“亲戚”。每次老秦回家,没过一天,他就问,“老秦,你啥时候走呀。”“老秦,你睡到我床上了,以后就不让你来。”为此,他经常挨母亲的揍,“老秦是你叫的么?老秦是你爸。”当哭着叫老秦爸爸时,他对眼前抚摸他脸颊的男人,才有了些许亲近。可还没等这种亲近升华,老秦就又进山了。慢慢的,叫老秦比叫爸爸还顺口。
老秦从早上开始就站在山梁上不停地捕捉儿子的身影,再过一会,典礼仪式就要开始了,到时就没法接儿子了?昨天他们忙得一团糟,搭台子、挂条幅、调音响,所有的人都忙得热火朝天,到了晚上好些人还要去上夜班,要不是因为这样,老秦就能找个哥们代替自个。昨天,项目部接到村长的“命令”,说镇里计划引资在这儿搞个温泉山庄,明天镇领导就要陪同市里领导要来视察工作,镇里要求村干部们和工地上的钻工必须在24小时里筹备好剪彩仪式。今天实在脱不开身,要不然他就能借辆摩托,到山脚接儿子。
正午时分,典礼仪式开始了。在台子中央,领导们轮流讲话,市领导表扬镇政府、村委会有眼光有魄力,能抓住机遇有所作为,造福一方;镇长表示将不负众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运作好温泉山庄这一扶贫项目。台下的老秦啥都没听进去,时不时回头看看空荡荡的山梁,寻找儿子熟悉的身影。
秦胜利此时正站在队伍后面,正聚精会神地听着高音喇叭里洪亮的声音。村长,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几乎是扯着嗓子说“我们村子能打出温泉,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钻工师傅们,花得是打机井的钱,竟然打出了地热。真得太划算了。我向各位钻工师傅们保证,工程款到年底付清。村子里再困难,也要响应中央精神,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村长话音刚落,会场响起最热烈的掌声。秦胜利听到工人师傅们私语,“数村长这句话最有水平,最给力了”。
秦胜利转身来到离典礼台两百米远的小山凹里,在那里,他看到了钻工们居住的帐篷。帐篷里最惹眼的就是四五张粘满苍蝇的“粘蝇纸”、横七竖八的晾衣绳,十多个东倒西歪的啤酒瓶,再有就是夜班钻机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听到远处的喧哗,看着此处的寂静,胜利的眼睛有点儿湿润了。典礼仪式结束了,一群身穿橘红色工服的钻工们正朝这边走来。秦胜利努力地寻找老秦的身影,直到一个老伯笑眯眯地走到他面前,“你是老秦的儿子吧。跟你爸说的一模一样,180高个,粗眉大眼高鼻梁,真不赖。转眼间就成这么大了。我们不服老,都不行了。”
“我……爸呢。”
“仪式一完,他就跑到东边的山头找信号去了。他还一个劲地嘀咕,说你可能不来了。天气这么热,连我们这些受苦人都受不了。没想到,你真来了。”老伯给秦胜利指了指远处的山头,“你爸绝对在那儿。那儿,手机信号最强。”说完,老伯扯开嗓子,冲着远处大喊,“老秦,老秦。你儿子来了。不用打电话了。”
远处黄土岭上,一个黑影从山梁上跑了下来,身后是滚滚尘土。老秦粗壮的声音由远及近,“啥时到的。吃完饭,爸带你去看钻机。”
刘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