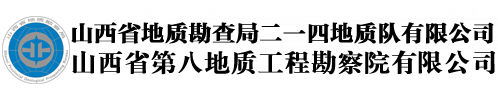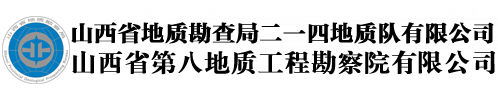在我国秦汉及先秦的典籍中,江、淮、河、济四水被称为四渎,而且“河”为四渎之宗,地位相当于大夫。所谓“渎”,《尔雅》说是“发源注海者也”,指具有独自的河源,而且直接流入海洋的河流。四渎中的“江”就是现今的长江,“河”就是现今的黄河,“淮”就是淮河,“济”就是济水。
时至今日,淮水已有多次入江而不直接入海的历史,济水由于黄河河床的移徙,其下游早已被湮没。“四渎”实只剩“江”与“河”了。这“河”,在秦汉以前是黄河的专称,而不是流水河道的通称,这可以在先秦古籍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如《尚书·禹贡》中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北至于砥柱,东至于孟津。”《山海经》中说:“河出昆仑之虚。”《诗经·卫风》说:“谁渭河广,一苇杭之。”《诗经·陈风》则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鲂!”《论语》说:“河不出图。”《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春秋左氏传》说:“河为崇。”等。这其中的“河”,都是指的黄河。
至于河流的通用名称,在先秦典籍中被称为“川”。如那句最有名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周礼·职方氏》在历述全国的河流时,也是用的这个“川”字:“扬州,其川三江”,“荆州,其川江、汉”,“豫州,其川荥、雒”,“青州,其川淮、泗”等等。《庄子·秋水篇》中的“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也说明着这一点。这里,“川”就是河,而“河”却是黄河。
在前汉时期,黄河仍习惯地被称为河,而无黄河之名。成书于汉武帝征和年间(公元前92年到公元前89年)的《史记》中,全书中找不到黄河一词。
但也有人认为“黄河”一词早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出现,并举《汉书》的《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以下简称“汉表”)中所载的汉高祖刘邦大封功臣的“封爵之誓”为证。这个誓词是这样写的:“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爱及苗裔。”它的意思是:即使到了黄河变成像衣带一样的小河,泰山变成只有磨刀石那么大小,所封的国土都永远存在,一直遗传到子孙后代。先不说这誓言是否真能兑现,但这几句话倒是很符合地质学的观点:
河流和山岳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河流会逐渐消失,山岳将被最终夷平。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黄河”一词便无疑出现在汉高帝六年了。
但是,只要核对一下司马迁的《史记》,在其《高祖功臣年表》(以下简称“史表”)中,你便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对于同一件事,即刘邦大封功臣的“封爵之誓”的“誓词”却是:“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爱及苗裔。”不同之点是:第一句少了一个“黄”字,第三句是“永宁”而非“永存”。显然,“汉表”对“誓词”进行了文字修饰。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学者王念孙(1744年~1832年)早已注意到了。他考证后,提出《汉表》中多出的“黄”字,是后人加上去的。
不过经笔者考察,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常山郡·元氏县”的释文中也已用了“黄河”一词:“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穿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堂阳为今河北省新河县。此黄河为西汉末年黄河改道以前的河道。因此,将“使河如带”改为“黄河如带”的,很可能就是班固自己,而不是更往后的人。在东汉时期黄河已开始姓黄了,而“河”这个字也渐渐取代了“川”的地位,被用作河流的通称。
《后汉书·郦炎传》载有郦炎所作的诗。诗中有“韩信钓河曲”这样的句子。唐朝为《后汉书》作注的李贤注意到韩信钓河曲是在淮阴城下的淮水,并没有在黄河钓鱼,所以他注释到“河者,水之总名也。”这固然是唐人的理解,但看来也符合东汉的实际。从“河”到“黄河”之间应该有一个转变过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始于东汉而确定于唐代?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一词且常见于文学作品,如西晋文学家成公绥的《大河赋》中有“览百川之弘壮,莫尚美于黄河”之句;梁朝范云《渡黄河诗》,以黄河为诗题。北魏学者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中的“河水”注中,也多次使用了“黄河”一词,不过用“河水”一词的次数还是更多。到了唐代,人们常用“黄河”,而把“河”作为河流的通称。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和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都是妇孺皆知的名句。
河水是何时变黄的
如果说“黄河”的名称始于东汉,是不是说河水在此以前不黄,最早到汉代才开始变黄的呢?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已有文字记说河水不清了。《左传》襄公八年(前565)郑国的子驷就引《逸周诗》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可见,黄河之不清早已为人所知。但也有说它清的,如《诗经》的《魏风·伐檀》一诗就有“河水清且涟漪”的句子,这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时候。
一般说来,黄河是浑浊的。《尔雅·释水》说:“河出昆仑,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这里认为河水色黄是由于所并入的河流太多的缘故。这就触及到一点地质问题,但不完全,因为它没有归因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
不过,河水的黄色引人注目,以至于人们用“黄河”来称呼它,却显示出黄河的含沙量在汉代有了增加。如在汉朝中期有位大司马史叫张戎(字仲功)的说:“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这是在汉早期还没有人说过的现象。在前汉中期以浊流闻名的是泾水。在汉武帝时,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在那时,引泾水来灌溉农田,还有改良土壤的作用。泾水和渭水流域,是黄土高原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而随着这种开发,原始植被受到破坏,水土流失加重,致使河水愈来愈浑浊,大概发展到东汉时期变得显眼了,从而有了“黄河”之名。河水水色变黄与黄河得姓,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
“黄河清”是怎么回事
根据清代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所载“河清”资料及笔者查到的其他记载共得43次。“河清”记载首见于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最后一次则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虽然可能仍有疏漏,想必也不多了。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为何清乾隆以后就不再记录河清之事了呢?在未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看看清代雍正、乾隆二帝对“河清”的态度与认识,可能对问题的分析与理解有所帮助。
先看雍正。雍正四年河道总督齐苏勒、副总河嵇曾筠等奏报河清之后,雍正谕旨说:“以休征叠见,稽诸史册,咸称福庆。而受宠若惊、不以为喜,实以为俱。惟有君臣益加勉勖。一德一心,以承眷顾。若先行庆贺,则沿袭颂美之虚文,大非承敬之素志,专遣祭告景陵(康熙陵)。专遣大臣致祭河神、内外大小官员各加一级。”谕旨虽有谦慎的话,但认识和行动与历代帝王所行没有两样。
对于乾隆五十三年的“河清”,乾隆帝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不但没有给予“大小官员各加一级”的奖励,还对奏报的山西巡抚明兴进行了一番训斥。原文较长,现摘录于下:“此不足为夸美,已于摺内批示矣。国家景运光昌,太和翔洽,惟在年谷顺成,丰绥屡告,五风十雨,普被和甘,乃为升平瑞应。至历代史策,侈陈符瑞,大率出于傅会铺张,无关实政。即如麟游凤翥,固为仅见嘉祥,然亦必须来游胄陬泽,翔集殿庭,得之目睹,方足传为盛事。若不过腾章入告,并无根据,亦止属粉饰虚词,不足为信。至河水澄清,虽亦间有之事,但似此侈陈祥瑞,夸示休征,殊属无谓。况上年黄河抢睢州十三堡地方,堤工漫溢,淹没田庐,甫经堵筑完竣。若以河清为献瑞之验,又何若安流顺轨竟无漫溢之更为嘉瑞耶。且河水澄清,如以为地方大吏德政所致,则明兴历任地方毫无整顿,试今伊自思:前在山东何无嘉应,今署晋抚又行何德政,而能致此祥瑞耶。封疆大臣惟应实心任事,承流宣化,使吏治民生共臻上理方为称职。倘因此等事属仅见,胪陈祥应,即宣布史馆,予以褒嘉;而遇有灾祸,即加之督责,势必至身任封圻者,藉端粉饰,争相效习以博虚名,而于地方水旱偏灾,或恐干谪谴,竟至讳匿不报。于政体民生大有关系。现在晋省既有河清之事,则下游各省,自必由渐澄清。该地方官不奏则已,倘亦有似此具奏者,再将此意,明降谕旨,以示朕敬天勤政,以实不以文至意,将此先谕明兴知之。”
乾隆的这一道谕旨,基本上说明了上面提出的问题,极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一特殊现象。而雍正的作为,未免仍是重演历代统治者的欺人故伎。现在,我们对于“河清”,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首先,历史上关于“河清”的记载,肇始于东汉晚期,说明在此以前,相对来说,河清现象可能比较习见,并非异事。同时,自东汉以来,黄河含沙量增加,浑浊更甚,故“河清”便成为国家的祥瑞,笔之于史。清浊是相对的概念,说河清,只不过比平时水色较淡而已,所以记载中说河清到“纤鳞毕见”、“澄莹见底”、“清如井水”的情况并不多。此外,“河清”出现的时间大都在夏涨之前,或秋汛之后,大多出现于冬季和春季,特别是农历十一二月枯水季节。在比较干旱的季节里,水土流失较微,所以出现较清的水色是有可能的。由于历代都把“河清”作为国家的祥瑞,并同当时的政治变化或斗争挂钩,故可能有些是不真实的。只是为政治需要而作,有的是地方官员为了升官晋爵的虚报,有的则可能只是谣传而已。
悬河是怎么形成的
黄河下游800千米的地上悬河堪称世界之最。悬河河床高度,相对于两岸河堤之外的平原,现已高出3米~5米,有的河段达10米。究其原因,乃是黄河夹沙量大,每年有约16亿吨泥沙的1/4堆积在这一段坡降不大、水流平缓的河床之中。
河底逐年淤垫,造成了悬河。
悬河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只要翻开历史考查一下它的原委,便可以知道并非自有河患以来即是如此。非但先秦至隋代时期不是如此,唐宋时期也非如此。在那漫长的岁月中,黄河下游基本上还是改道频繁的河流,入海之处或北或东或南,持续时间长短不一,但以北流入渤海为主。自南宋初年,即1128年(建炎二年)在战乱之中,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开封守将杜充决开黄河以阻金兵,才是黄河长期南泛夺淮入海的开始。而南泛的黄河,自1128年以后至元代的结束、明代的前期,并没有稳定的河床,只是分成多股的黄流,泛滥于豫中到鲁西南的广阔平原之上,或分或合,直至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出于保证运河的漕运畅通和每年江南数百万石粮食安全运抵京师北京的需要,必须稳定黄河河床,才使运河在徐州以南得以“引黄济运”。徐州以北又不受黄河决口、改道后对运河的冲击和破坏,又要使徐州以南黄河水入运河不致淤浅,阻碍漕运,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将治黄治运联系起来的方针。
明代万历年间的治黄专家、河道总理万恭在他的专著《治水鉴蹄》一书说得很清楚:“治黄河,即所以治运河,若不为饷道计,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复禹故道,则从河南铜瓦厢一决之,使东趋东海。则河南、徐、邓永绝水患,是居高建瓴水也,而可乎?”这就是说,治黄河就是为了治运河,使运道畅通,若不为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京,仅仅是为了免除黄河之害,只要河南铜瓦厢把黄河北岸决开,使黄河东走渤海,则河南、徐州、邳州一带,就会永远没有黄河水患了。因为这是高屋建瓴之势,非常容易达到的单纯治黄的目的,那样做行吗?能解漕运问题吗?这种观点完全改变了以往治黄治运不相联系的传统方针,在当时应该说是比较进步的吧。
要达到这样一种围绕治运而治黄的目的,采取的措施必须达到两个要求:即要黄河不危害运河,又要利用黄河之水补充运河。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第一步要在黄河两岸坚筑堤防,固定黄河河床,第二步要利用黄河之水力冲刷河床的积沙,使之不淤垫河床。反过来两岸的巩固堤防又成了来水攻沙的工具。
但实际运用中,由于黄河下游的河道平缓,并不能完全解决攻沙的问题,于是黄河河床还是不断地在逐年增高,两岸的河堤也随之逐年增高。经过从明朝晚期到清朝晚期300余年的积累,世界著名的地上悬河也就形成了。明代晚期这种“固定河床,束水攻沙”的方针提出并开始实行之时,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反对的意见,如当时的另一担任过总理河道的杨一魁便指出过束水攻沙有加强地上悬河的潜在危险。他认为“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年来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过颡,滨河城郭,决水可灌。”
与他同时的王立胜也指出:“自徐(州)而下,河县日高,而为堤以束之,堤与徐(州)城等。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虑也。”还有人指出“固堤束水,未收剧沙之利,而反致冲决”,或指出“先因黄河迁徙无常,设遥缕堤束水归槽。及水过沙停,河县日高,徐部以下,居民尽在水底”。但是由于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来治黄保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行了几百年,其结果是地上悬河越来越高,一旦决口,黄河之水天上来,悲惨的景象直到解放以前,历演不衰。悬河的威慑力量,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其阴影至今仍未消除。虽然黄河确实已在1855年(清咸丰五年)于铜瓦厢决口,东趋渤海;而南北大运河的漕运任务早已解除,我们治黄的方针、措施、要求等等,是否还有遵循明清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方向继续走下去的必要呢?
——摘自《中国矿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