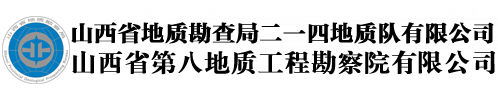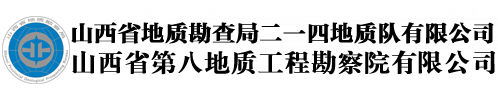其实,我不喜欢父亲。
自打我记事起,他就总一把一把的吃药,羸弱的身躯藏不住暴躁的脾气。在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因我太能哭闹,他顺手抓起手边的竹筷冲我脑袋上就是一下。那股子钻心的疼痛如今早已记不起来,高隆的红肿也消失不见,但他可怕的模样却清晰的烙印于我脑中,挥不去抹不掉。母亲说他只是年少为父,才会此般不懂得疼惜。
儿时父亲近乎严酷的形象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如同一颗灰色的种子在我心中肆意疯长,成为横亘父女之间难以逾越的屏障。在我记忆中,他对母亲多数时候是很严厉的,纵使在我眼中饭店无法媲及的佳肴,在他口中都挑得出毛病。 他年少时不知爱惜身体,落下风湿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疼痛难忍,母亲总是在他之前起床,温备早饭,尔后侍奉穿衣,而他却总叫嚷不够周全,母亲便慌了手脚无所适从。我总觉着是身体的缘故,才让他离不开母亲的,他需要有人打理衣食起居,却并非因为感情。
直到那年母亲得了急症,需要住院动刀,我对他的印象才有所改观。母亲住院那段日子时,他无暇自身腿疾,近半年时间里来回奔波,从未进过厨房的他还亲自为母亲煲汤熬粥。在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后,他故作轻松说让我放心。我看到他额前细密的汗珠,便问他“你怕么”?他大笑,攥住我的手说“傻孩子,寻常手术而已”。说罢,便转身踱步坐回病房中。他掌心的冷汗残留在了我的手中,我第一次感到父母间的爱远非我简单看到的那样。后来,母亲告诉我,他们的感情早已深入骨髓,她从不埋怨父亲的暴燥,在她心中,夫妻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她说父亲受了太多苦楚却能忍常人所不能,她说父亲很疼我只不过嘴上不曾说。母亲看到我的疑虑,讲给我一些我不曾了解的过去。
父亲是个测量工,在我还未记事之前他都仍为地质事业卖着命,年少轻狂总觉着身子如铁打般不惧冷暖,饮山泉沁凉水、卧严寒刺骨石,一腔热血总能抵挡野外生活的艰辛。然而爷爷病危之时,他不顾众人劝阻硬要抽血供给,即便如此仍无力回天,爷爷病逝,父亲也病倒了。抽血后的虚弱加之操劳过度,轻易击垮了这严寒侵蚀过的身体。我记事以来,便知道父亲终日卧床不起,我听不到他疼痛的呻吟,只能从他变形的关节和与日俱增的药剂看得出这疾病的折磨。
印象中我从未像其他孩子那样骑在父亲肩头嬉闹玩耍,也没有被父亲接送去过学校,甚至他都不曾牵过我的手随处走走。在我心中他是那么威严不可亲近,而他却把他那柔和细致的一面透过母亲传达于我。他知道怎样的饭菜更合我胃口,哪时的气候我容易过敏感冒,他随时关注我上学的城市升温还是下雨,担心不在身边我会不会缺钱受委屈。这一切的好意,我一直都记在母亲身上,对比之下,更衬得父亲冷漠有距离。其实我早该知道的,只是他满眼的疼惜我都不曾凝视过。
记得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埋怨他不准我远行,便嚎啕大哭不听劝说。无意间,我瞥见他背过身去,用衣袖拭泪,伴着浓重的鼻音从喉腔抖出句话,让我至今想想都眼角湿润,他说“还不是舍不得你在外受苦”。然后我便妥协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读书,小假长假都乐颠颠的往家跑,母亲总是做一桌我爱吃的家常菜,笑着抱怨我离不开家,而他却只坐在一旁,不轻不重的道一声“回来就好”
世界上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细细想来,其实父亲的爱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周围,如同包裹我的空气,不拥挤不甜腻,只是自己不曾觉察。他有时无意的疏远冷落,也许仅是因着他不想让女儿看到他锥心的病痛。
当我再次好好端详父亲时,这才发现他已不再年轻,他满头锃亮的黑发变得银灰柔软,他不苟言笑的面庞褶皱满刻,卸去的棱角也带走了他傲然的霸气,路遇伶俐的孩童,他的脸上毫不吝啬慈爱的笑容。父亲老了,我的心里还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呢。
每次下班回到家里,父亲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漫不经心的嘘寒问暖,不咸不淡却温暖窝心。他羞于表达,却用最含蓄最质朴的方式让我感受他最淋漓的疼爱。他总是告诫我要少说多听,要么一鸣惊人,要么沉默是金。就这样耳濡目染,我渐渐褪去学生时代的稚气,修身养性、完善自我,更是静得下心也拿得出手,不怯懦不恐慌。
今天是他的生日, 每每送他礼物,他都总不言不语,像是从未送到过心上,再精心挑选都难博他一笑,那就拿此文献给他吧。
生日快乐,老爸!愿您乐以忘忧,福寿康宁。
(谢志娟)